泰山尼姑,被迫卖淫代孕的一生(组图)
最近,一则旧新闻震撼全网。
新闻来自1935年的报纸,只在版面上占据了小小一个方块,看似平平无奇。
标题是《尼姑出租代人生子》,里面讲的是泰山尼姑靠代孕谋生。
“没有儿子的人们,可以到庙里去选一个小尼姑,期限三个月或半年,在这期间里只担任她的衣食。”
“要是怀孕而能生子的话,租的人就可以付给相当代价(大概自几十元起以至百余元止,这要看尼姑美丑而言),要是没有怀孕,只须随便给一二十元就行了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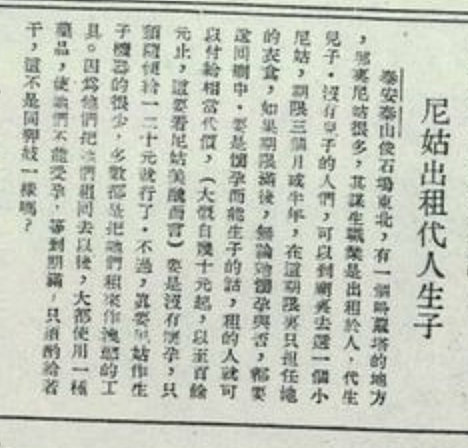
这里是五岳之首,道教佛教胜地,供奉的香火从古至今鼎盛不绝。
然而,这里的尼姑却要为了谋生出租子宫。
据新闻所说,用作生子机器的都是少数,大多是把她们租来做泄欲的工具,可以使用药品让她们不能受孕,到期后只须“酌给若干”。
这未免太挑战常识了,我们印象中的尼姑应是修行之人,每日吃斋念佛、守戒禅定。
然而,络绎不绝的香客将泰山的石阶磨得光亮,也将尼姑庵变成另类的风月场。
泰山姑子,沦为娼妓。

佛门圣地,竟是善男的妓院
在清末小说《老残游记续》中,讲述了老残一行四人游历到泰山的见闻。
他们途经一座叫斗母宫的尼姑庵,想进去讨个斋饭,走进客堂才发现别有洞天。
这里简直是建在山脚下的招待所,不仅装潢精美,雅座包厢一应俱全,姑子还能下厨给他们做荤菜。
走进一间闺房,对联上写的是“靓妆艳比莲花色,云慕香生贝叶经”,这是一则藏头联,写的是名叫靓云的小尼姑的花容。
用如此字眼形容一位尼姑,初来乍到的老残一行人觉得稀奇,询问靓云的踪迹才得知她下乡去了。

另一位尼姑逸云解释道,这个庙原是为了招待上山烧香的官绅文人,陪他们喝酒聊天。
可,光是喝酒陪聊还不算完,有的甚至要停眠整宿。
那位名叫靓云的小尼姑,才十五岁,因为模样俊俏被泰安县大老爷的少爷看中,时常被要求陪睡,甚至大发脾气:“今儿晚上如果靓云不来陪我睡觉,明天一定来封庙门”。
忌惮于大少爷的威风,靓云这才被送下乡去,惹不起躲得起。
和我们现代人对寺庙戒律森严的认知不同,斗母宫里的尼姑虽然名义上是尼姑,但做的是皮肉生意,是佛门兴盛所催生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娼妓。
在徐珂创作的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《清稗类钞》中,也有泰山姑子的身影:
“泰山姑子,著称于同、光间。姑子者,尼也,亦天足,而好自修饰,冶游者争趋之。顶礼泰山之人,下山时亦必一往,谓之‘开荤’。盖朝时皆持斋,至此则享山珍海错之奉。客至,主庵之老尼先出,妙龄者以次入侍。酒阑,亦可择一以下榻。”
“可择一以下塌”,讲得够直白了。
香客上山游览泰山结束后,返程途径斗母宫,就要在这里大开荤腥,这个开荤不仅是口腹之荤,也是色欲之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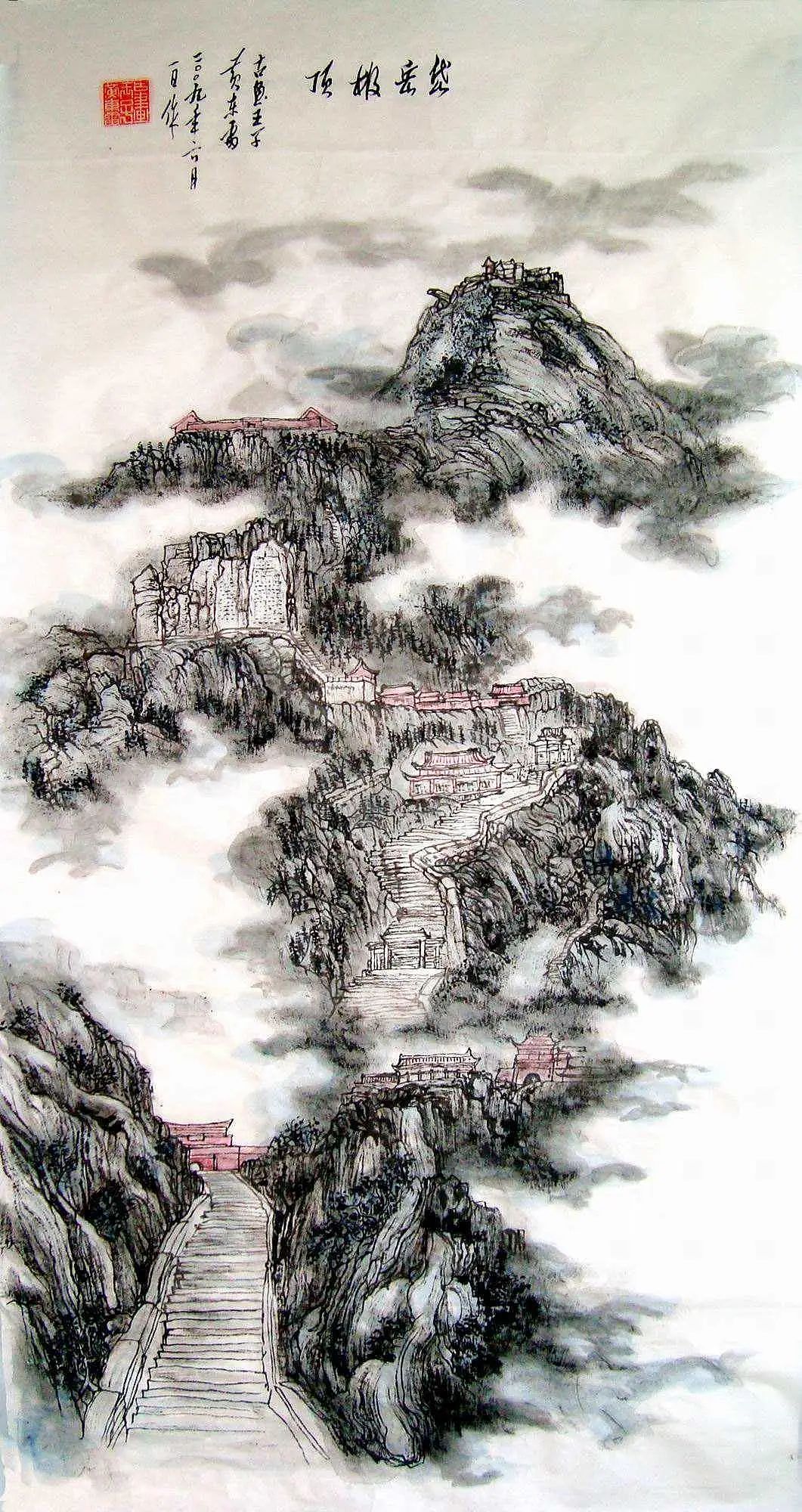
上山修行,下山嫖娼,修禅的戒律都维持不到出泰山,在山脚下就统统打破还俗。
以斗母宫为首的尼姑庵,有点像如今的色情洗浴中心一条龙服务的下游,负责为香客破戒解馋。
有盛赞说,“泰山的尼姑,不仅京泸名娼不及远甚,就是天南地北,也找不到第二处”。

古代四大“制服诱惑”?
泰山尼姑艳名远播,却争议不断。
有人爱她们“幼尼皆妙婉秀丽、解文识字,衣装如美少年”。
有人恨她们尼姑从妓,有伤风化。斗母宫大门附近就有山石上刻了“虫二”二字,是济南才子刘廷桂爬泰山时题写。
听说这里的尼姑如此不尊佛礼,他大为愤怒。风月无边,是为“虫二”。

可,骂一句浪荡妖女,叹一声“以色事人就是贱”,就够了吗?
来到斗母宫谋生的女子,不过是来自当地家贫而貌美的女性。地方官绅乐于享受风月,民间百姓淫靡之习弥漫,而斗母宫的姑子,成了为这一切买单的存在。
《老残游记续》里,嫁到富贵人家为妾的尼姑,最终被人折磨至死。
从妓、代孕、出典,被底层社会层层盘剥的泰山尼姑,又有几人能真正摆脱悲苦的宿命。
名妓背后,尽是血泪。
然而,出名的古代名妓除了「泰山尼姑」,还有「扬州瘦马」「大同婆姨」和「西湖船娘」。
其中,扬州瘦马最为出名。
明清时期,盐商富贾聚集在扬州地区,为了迎合他们的性需求,养瘦马这个产业在暗中兴起。
所谓养瘦马,其实就是人贩子买来的出身贫寒、相貌姣好的幼女,一般在5到14岁之间。
因为这些女孩大多瘦骨嶙峋,所以得名为“瘦马”。

买来的女孩被分为不同等级,经专人调教为不同功能的性工作者。
一等资质的女孩们学习“弹琴吹箫,吟诗写字,画画围棋,打双陆,抹骨牌,百般淫巧”;
二等资质的女孩,被培养成财会人才,懂得记账管事,以便辅助商人,成为一个好助理;
三等资质的女孩不让识字,只习些女红、裁剪,或是“油炸蒸酥,做炉食、摆果品、各有手艺”,被培养成合格的主妇。
如此“专业”的培训,不过为了过几年能卖个好价钱。比如《绣春刀》里杨幂饰演的北斋,原是罪臣之女,后被卖到扬州成为瘦马。

而西湖船娘,则是发迹在船上的娼妓,又称为“船妓”“莲娃”。
隋炀帝开凿运河下扬州,因为喜欢看美女摇橹的倩影,便广招女性船手,白天摆渡,晚上侍寝。
这些船娘大多是江南渔民人家的闺女,年幼时就被父母卖给掌管水上生意的“妈妈”,长大后送上花船卖色卖艺。
《还珠格格》里的夏盈盈就是船娘出身,在花船上卖艺为生。

不少声名显赫的文人骚客,都爱极了这“西湖水滑多娇娘”。
家妓成群的大嫖客白居易,就曾在《宿湖中》一诗中感慨:“幸无案牍何妨醉,纵有笙歌不废吟。十只画船何处宿,洞庭山脚太湖心。”
写的就是他在太湖上狎妓的日子。
何其快活,甚至写诗给自己的“好嫖友”元稹显摆,“报君一事君应羡,五宿澄波皓月中。”
还有苏轼、秦观、王微、柳永......西湖船娘在无数文人雅士笔下被书写,成为肤若凝脂、软玉温香的代名词。
然而,被当作景观赏玩之余,又有几人关心她们命薄如纸呢?
与扬州瘦马和西湖船娘不同,大同婆姨,是丰乳肥臀系娼妓代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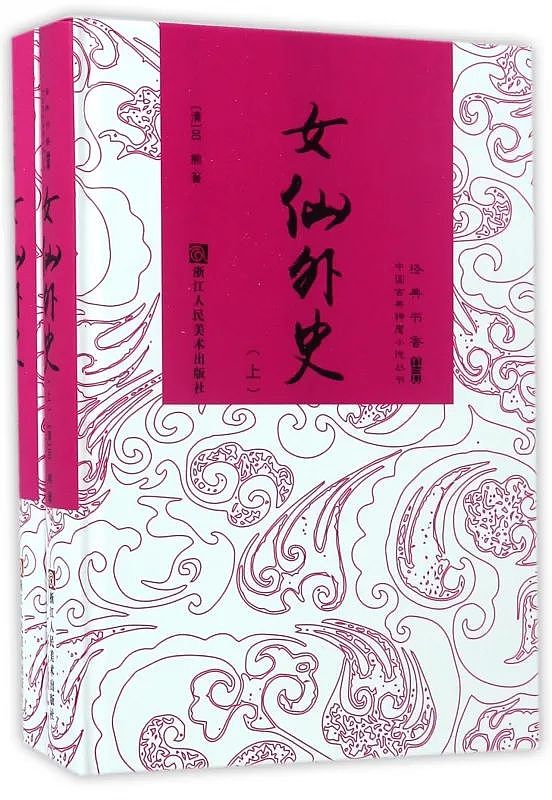
《女仙外史》中的名妓柳烟,就是“大同婆姨”
大同婆姨从小便要练习一门童子功——坐瓮。老鸨为女孩们依据体型差异挑选一口合适的水瓮,每天沿水瓮而坐,一直坐到十三四岁。
这般类似裹小脚的肢体虐待,只是为了让她们变成最好的人形“飞机杯”,提供完美的性服务。
有文人在三重门上题联,夸赞她们床技精湛:
第一重门,“鸟宿林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,匾曰“别有洞天”。
第二重门,“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,匾曰“渐入佳境”。
第三重门,“云无心兮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”,匾曰“极乐深处”。

好个文雅嫖客,寥寥几笔,就把嫖娼变成了“文学”,变成了“艺术”。
所谓泰山尼姑、扬州瘦马、西湖船娘、大同婆姨,与其说是四大名妓,不如说是古代男性为了满足淫欲,在各行各业依照不同口味打造的嫖娼天堂。
直到今天搜索相关内容,依然能看到许多男性感叹,“原来古代就有制服诱惑了啊”“泰山尼姑就是最早的佛媛了吧”。
是啊,在我们看来,那是无数女性的悲苦命运和颠沛流离,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句,“今不如昔”。

被掩埋的娼妓之苦
回顾历史,到处都是类似这样吃女人的注脚。
无论古今中外,父权都在默契地合理化殖民女性身体这件事。
妓女,或许是可考的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,在宗教祭祀诞生之初,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就开始了。
古巴比伦,一个缔造了璀璨文明的梦幻国度,对待女人却极尽剥削。
古希腊人希罗多德在《历史》一书中说到:“在巴比伦,从王室到民间,每个女性一生必须做一次妓女”。

在巴比伦的阿芙罗狄忒神庙,无数女性,无论平民或是公主,都要在这里完成一项伟大的仪式,做一次“圣娼”,将用身体赚来的钱捐给神庙。
以宗教之名,无数女性被祭司们掠夺了身体的主动权。
我们现在感叹泰山尼姑的存在有辱佛门清净,但事实上,宗教从来都是高度父权主导的领域,他们同样在物化女性,只不过用一种更神圣、更隐蔽的方式。
在许多古老宗教的风俗里,女性需要通过献祭自己来表达对神的忠诚。
在印度,有献祭圣女的惯例,漂亮的女孩被选为圣女,她们被安排学习宗教礼仪,被灌输自己的职责就是“侍奉神”。
表面上她们是被信徒顶礼膜拜的宗教吉祥物,实则,她们是服务长老、僧侣的僧妓。

美国臭名昭著的邪教FLDS,女性从生下来就被灌输一生职责就是结婚生子,甚至出现65女共侍一夫的离谱画面。
神父强奸幼女时口头依然念着:“以圣职者对权力,透过其中的钥匙和力量,和圣职者及天堂合而为一”。
女性的肉体,是男性通往上帝的道路。

那些看似“伟大”的人类文明果实,为何落实到女人身上总是殊途同归——
成为娼妓,献出身体和子宫,无论同意与否。
文艺复兴这样划时代的存在,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妓女行业的大爆发,使得卖淫成为“必要的邪恶”。
1490年的罗马,几万人口中就有约7000名妓女,卖淫比例之高。甚至政府都明令鼓励开办妓院,美其名曰帮助男人们“看见上帝”。
作为文艺复兴前奏的十字军东征伊始,就早已预示着这一切。
《文明的阴暗面:娼妓与西方社会》一书中写道:“十字军东征有成千上万的妓女跟在身后,每个营地都养着自己的大妓院”。

然而,在主流叙事中,女性的遭遇被轻而易举地掩埋过去。
女人变成物件,娼妓变成景观,无数女性的血与泪,变成漫长人类文明史上的小小装潢画。
所谓历史,无时无刻不是踩在女性身体上往前行进的。
还是戴锦华老师那句老话:
「迄今为止,这天是男权的天,这地是男权的地,这文化是男性的文化。历史就是his-tory,没有her-tory。」
别忘了,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,妇女和女童的权益才被纳入人权保护范畴,距今还不到三十年。
站在此刻回望过去,满眼皆是女人的尸骨。
所以,别轻易吞下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,还有太多苦难,被遗忘在书本的另一侧。
我们能做的,唯有将苦难从坟墓里掘出来,一遍又一遍。
起码在我们这个年代,她们重新被人看到,被人书写。





 +61
+61 +86
+86 +886
+886 +852
+852 +853
+853 +64
+64


